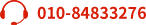文 | 罗洁琪
1
这是第三次,张媛决定把灯打开。灯亮了,趴在她身上的男人急忙翻下床,跪在地上,向她求饶。他说,是她的丈夫半夜输了钱,让他来睡她抵债的。
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两次,前两次的男人是谁,张媛也不知道。他们都是在她熟睡时,用钥匙开了门,摸黑进来,爬上床和她发生性关系。她才新婚三个月,对丈夫的身体还不熟悉。那是1998年前后,在河北的农村,还不流行婚前同居。第一次,她以为是丈夫。过了一段时间,又有男人深夜进来,好像和上次不同,她开始感觉到异样。
丈夫嗜赌如命,是河北省一个化工企业老板的儿子,纵然如此,也不够钱挥霍。他深夜赌钱,彻夜不归。张媛害怕,就在枕头底下藏了一把剪刀。
第四次,她确认了,是她丈夫。她问,“前几次是谁?”他回答,是赢了钱的人。丈夫强行要跟她发生关系,愤怒、屈辱的张媛极力反抗,混乱中拿起了剪刀,尖刃划破了她丈夫的动脉,血流如注。急救车赶过来时,男人因失血过多,抢救无效。
几个月之后,全国妇联维权处处长徐维华的办公电话突然响起,国务院妇儿工委的一个领导说,“维华,河北发生了一个丈夫强暴妻子,反被妻子杀死的案子,原因很复杂”,她指的就是张媛一案,那时,一审法院已判处张媛死刑立即执行。简单讲述了案情,领导叮嘱,“那个妇女太冤了,你看看,我们怎么样为她发声,能让法院枪下留人?”
了解了案情之后,徐维华判断,“丈夫把老婆当筹码,找人强暴自己的老婆,就是严重的性暴力!”张媛既是杀夫案的被告,也是强奸案的受害者。如果撇开强奸案,单独审理杀夫案,就无法查明事实真相,更加不能适用死刑。
徐维华将张媛亲属给妇联的求助信和材料分别转给河北省高院刑庭、最高法刑庭。她提出“请查清案发原因,背后真相,根据案件具体事实,若亲属反映属实,应慎用死刑”的要求。同时,她联系了最高法的刑庭法官,积极地表达全国妇联对这个案子的关切。她认为,妇联虽然是权力边缘部门,可是嘴巴还是很厉害的,就是给各个部门做协调工作。“积极发声”——这是徐维华的口头禅。
她发现,张媛婚内遭受性暴力而杀死丈夫,一、二的判决显然对杀夫案的关键因素没有彻查清楚,认定事实有误,量刑失当。于是,她继续和最高法的法官沟通,请求慎用死刑。2007年以前,死刑复核权还在省高级法院,尚未回归最高法院。最高法的一个法官对徐维华表示,一定向河北高院转述妇联的关切,在案件报备的过程中,最高法会尽职依法。
在二审判决前,徐维华要去香港参加一个会议。她特意给最高法的那个法官打电话解释,“等回来再继续联系”。7天后,电话再接通,张媛已经被执行了死刑。死的时候,新婚不足一年。
“她是被冤死的,她的在天之灵,不会放过那些人”,2009年春天,张媛去世20年后,徐维华仍然叹息,“每次想起她们,都于心不忍”。
“她们”,是徐维华在全国妇联工作时协调过的几个家暴受害者,她们都曾像张媛一样反抗,最后也都成为死囚。徐维华多次想枪下救人,然而,失败居多。她说,“那个年代,很多公检法人员对家庭暴力的常识几乎为零,更加不知道什么叫受虐妇女综合征”。
2
徐维华今年70岁,短发花白,精干爽朗。她穿浅蓝色牛仔裤,休闲的T恤和夹克。她喜欢背着双肩包上班,笑容温暖,有很强的亲和力,举手投足之间,常常带着对旁人的关切。
徐维华学法律出身,曾经当过警察,也做过高校里的法学教师。1983年,她调入全国妇联维权处,在那里工作了20年。她说,妇女的困境给予了妇联以使命,为妇女工作,既是幸运,也是命运。
妇联的工作,说得最多的是保护妇女的安全和健康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,妇联组织起草《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,1992年出台。在立法者的眼里,家庭暴力并不是紧迫的妇女困境。那部法律对家庭暴力,只用了几个条文进行宣示性立法,即禁止、预防和制止家暴,连家庭暴力的定义都没解释,更加没有规定救助措施,证据规则和对施暴者的限制等。受虐妇女的心理创伤,更是一片被忽略的空白。
1995年,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,那次会议改变了很多妇女权益研究者对家暴的理解,包括徐维华在内。
会议很隆重,参会人士来自189个国家,将近6000名的政府代表,约5300名非政府组织代表,召开了数千个分论坛。盛况空前,人头攒动,各种肤色的面孔都有,在众多论坛中,徐维华被安排去了一个关于维护妇女权益的论坛。
会务组严格控制人数,参加论坛的都是重要的专家,还有顶尖的律师,全国律师协会《中国律师》杂志社主编助理郭建梅在会议上采访,听了希拉里的演讲,旁观了与会者的讨论,被议题的人权魅力深深吸引。参会者交流着各自国家妇女的境况,特别是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。家庭暴力,这个名词和相关理念,从那次会议开始流入了中国。
中国传统的思维是清官难断家务事,甚至在当下,很多判决书里仍把家庭暴力表述为“家庭纠纷”。在那次会议上,徐维华听到一种声音:家庭暴力是一种基于性别文化的暴力,它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家务事,而是需要公权力介入的人权问题,包括身体暴力、精神暴力、性暴力和经济控制。
世界妇女大会以后,全国妇联和国外的机构合作调研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,其中一项就是关于家庭暴力。结果让人惊讶,在离婚案件中,有超过30%的婚姻存在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。调查问卷覆盖有限,徐维华认为,实际数量肯定会大得多。
“培训是第一位的”——这是全国妇联的第一个反应。她们开展了关于反家庭暴力的培训。医务人员、基层妇联干部、公检法人员、教育工作者,社会工作者和婚姻登记处的人员,是接触受家暴妇女的一线人员,被列为重点培训对象。
那是中国反家暴的启蒙期。几乎所有妇女问题研究者都知道,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卓有成效的民间组织——“反对家庭暴力网络”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院、中华女子学院、中国公安大学,中国政法大学,北京大学、《中国妇女报》等都是这个网络的会员,还有很多学者、律师和社工等个人会员。那是一个富有热情和行动力的反家暴社区。世界妇女大会结束后,第三个月,郭建梅就从杂志社辞职,筹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,开展民间妇女法律援助,免费为弱势妇女代理案件。从1996年开始,徐维华在业余时间支持郭建梅,一起合作。2003年,54岁的时候,她提前从全国妇联退休,去了反家暴网络担任办公室主任,为重大的反家暴个案提供法律援助,组织各类培训。
一年半之后,她应邀去了郭建梅创立的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中心。她还成立了北京徐维华律师事务所,以律师的身份代理案件。
俩人既是故友,也是旧同事,郭建梅曾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。她们多次合作办案,最惊险的,是为四川受虐妇女李彦杀夫分尸案做辩护。
3
2012年,死囚李彦命悬一线。
李彦生于1971年。2009年3月,她和谭勇结婚,俩人都曾住在安岳县蚕桑局的宿舍楼里,相识多年。李彦是再婚,她有一个孩子,在寄宿学校读书。谭勇比她大几岁,曾离婚三次,有两个儿子。很多邻居对李彦说,三个老婆都是被他打跑的,他品性不好,脾气烈。
可是,李彦觉得他好,前夫长年无业,也不干家务活,她想找一个比自己大的人,懂得照顾自己。谭勇在追求她时,常常买菜做饭,甜言蜜语,说他也四十多岁了,坏毛病早就改了,以后会对她好。李彦的父母和姐弟都不同意,父亲更是气得要断绝关系。李彦一意孤行,相信了谭勇,结婚时,还向亲友借了两万多块钱,和谭勇一起买房买车,让他开车营生。一个老邻居说,她是“睁眼跳下了崖”。
婚后三个月,她回娘家,在同一个宿舍区的对面楼。妈妈发现了她身上的伤痕,就去了谭勇的父母家,希望能劝谭勇改掉打人的脾气。谭勇记恨,从那以后,不让李彦回娘家,也不让接娘家人的电话。
2010年6月5日,李彦在日记里写着:“今天是五月初四,也就是端午节的头天晚上。妈打电话叫我到她那边拿几个粽子。洗完碗后,我对谭勇说,去妈妈那里拿粽子,20分钟就回来。他没开腔。回来后,他大骂。我解释几句,招来又是一顿毒打,打得血像滴屋檐水一样。我赶紧跳下床,他还是继续打,一点不手软。鼻血往下滴,嘴巴里也一口口往外吐。这就是我的生活。”
在日记里,她隐去了一些觉得羞辱的事情。殴打后,常常在她脸上还滴血的时候,谭勇就强迫她发生性关系。
谭勇还限制李彦和其他人的交往,每个月只给20元的电话费,包括了月租。只要谭勇在场,李彦都不敢谈电话,匆匆两句就挂断。
婚前,李彦帮姨妈经营一个小卖部,有收入。婚后,谭勇就不允许她出去干活了。谭勇一般只给100元的家庭生活费,无论买什么东西,哪怕一根葱,李彦都必须记账。账不对,就遭来拳打脚踢。有一次,她买了超市的打折内裤,两条不到30块钱,谭勇拽着她的头发就往墙上撞。打了之后,把她关在阳台上,不让吃饭。这样的打骂越来越频繁,每个月都有几次,都是发生在夜里。有时候,邻居会看到李彦整夜地躺在楼梯前的走廊上。尽管她的妈妈就住在对面楼,她从来不敢回去。
李彦爱面子,不想被别人笑话,觉得再婚不容易,凑合过日子就是。
2010年8月的一个下午,李彦在隔壁邻居家里打麻将,谭勇突然出现。在众目睽睽下,抓起李彦的头发,往家里拽,用力很大,头发被扯掉很多,膝盖也磨掉了一大块皮,鲜血直流。邻居们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,还有李彦喊天叫地的求救。楼上的老职工听到了,对谭勇的侄子说,“快下去,下面出事了”。谭勇的侄子下了楼梯,在门口想进去拉架,被谭勇推出去,把门关上。另一个邻居就想从后门进去,被谭勇一脚踢在腰上。最后,谭勇还把李彦的东西往楼下摔。
李彦和她的妈妈都曾找过社区干部反映情况,对方建议她们找妇联。
安岳县妇联接待的记录显示:2010年8月3日,李彦到妇联反映,结婚一年多,遭毒打,想离婚, 谭勇性格偏执,不听人劝。婚前共同买的房子,在亲戚那里借了2万多元。妇联建议:找社区干部或者最信任的亲朋戚友,做一些劝导工作。保留好家暴的相关证据,以备起诉离婚时用。
安岳县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显示:2010年8月10日22时32分,李到派出所反映,当晚被丈夫打了,并且说,谭勇经常打她,有家庭暴力。派出所建议:向妇联反映。如果确实无法在一起生活,可向法院起诉离婚。
从社区到妇联,从妇联到派出所,派出所把皮球踢回妇联,妇联又把皮球踢回了社区。社区干部对李彦妈妈说,谭勇太厉害了,怕他以后找上门来,还是去找妇联吧。由始至终,没有一个机构曾上门找谭勇进行过训诫。没有反抗,也没有公权力的约束和惩罚,谭勇继续肆无忌惮。
既然派出所建议去司法局,于是,李彦就找好朋友陪她去过一次司法局,司法局的人说,“要结婚两年后才能离婚”。李彦觉得无望,就求谭勇离婚,给她一条生路。俩人协议离婚,谭勇要面包车,负责偿还15500元的家庭债务;李彦要房,负责25000元的债务。次日,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时,谭勇反悔了,并且威胁她,“如果再提离婚,就让你家破人亡”。
李彦害怕,再也不敢提出离婚了。不过,从那以后,李彦也开始留心保留家庭暴力的证据。2010年8月2日晚和10日晚上,李彦被殴打后都去照相馆拍了照片。照片显示,头、颈部有数处长达数公分的瘀紫伤痕。
偶尔,她还悄悄地写日记。“我心里很乱,也很矛盾......别人都说我变了,我变得我自己都快认不出来了,没有亲人,没有朋友,像一个囚犯,没有一丁点自由。处处小心,还要被监视......我好想坐下来心平气静和你商量沟通,我想绝对没有好结果,讨来的保证是一顿饱餐暴打....过二天就是中秋节了,我不愿让我的姐姐、弟、女儿看到满身伤痕的我,给我留一点点面子和尊严。”李彦在2010年的中秋前夕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,字迹清秀。至于谭勇对她的性暴力,哪怕在日记里,她也只字不提。
谭勇严格控制李彦的人身行为,自己却在外面沾花惹草。有一天,有人告诉李彦,谭勇和一个女人在茶楼幽会。她很生气地打车过去,却被谭勇带回家。他问,刚才是用哪个手指着那个女人?李彦说,是左手。他再问,是哪个指头。李彦伸出了左手中指。谭勇站在李彦的左侧,右手拿起菜刀,一刀把她左中指剁掉一节。在医院包扎时,医生说可以去成都的医院接指,谭勇不同意。
谭勇要求李彦对外人说,手指是砍猪脚的时候砍掉的。断掉的那节手指装在一个小瓶子,用福尔马林浸泡着,在一个鞋盒里,和她的日记本一起藏在阳台的杂物堆。
4
谭勇以前是开面包车的司机,有几个兄弟姐妹,妹妹在当地的报社工作,妹夫在政法部门。他和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在解放军某个部队服役。李彦认为,在当地,他们家算是有势力的家庭。
2010年9月左右,谭勇在安岳县柠都新城二期工地监管工人施工,李彦在旁边开了一个小卖部。虽然他们买了婚房,为了方便经营,就住在工地旁边简陋的平房里。一个木板床,放着棉絮,厨房里架起一块板,放着锅碗瓢盆和一口高压锅。每天晚上,李彦会用高压锅烧好开水,第二天一早,工人买方便面时要用。
11月3日的傍晚,谭勇的工友黄某来了小卖部,对李彦说,今晚多做一份饭,还有个工友要去吃饭。当晚,谭勇在看工人浇灌混凝土,黄某也告诉他了。深夜12点多,李彦在厨房洗碗,喝得醉醺醺的谭勇把花生米放在她头上的窗户,用气枪对着瞄准。李彦叫他不要在那里打,会打到她的脑壳。
谭勇说,“不打你的脑壳,就打你的屁股”,用枪对着李彦的屁股上。李彦哭着求他,他笑着走开。洗完碗,李彦用盆子打了洗脸水,蹲下来伺候谭勇洗脚。他坐在床边上弄枪,逼问李彦和黄某是什么关系。李彦回答,“你的老婆是啥样子的人,难道你还不清楚吗?”
“老子骂你几句,你还犟嘴”,谭勇一脚踢在李彦的左侧大腿上,再用枪管使劲砸李彦的右脚大拇指。
李彦痛得尖叫起来,“你不是要打吗?晚点我用棒棒跟你打。”
“你打嘛,你打嘛”,谭勇说。
“我打了哦”,李彦顺手拿起床边地上放的枪管,就砸向了谭勇的后脑勺。他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。李彦害怕他万一站起来,会继续毒打她,就又补了一棒。这次,脑袋流血了,她慌忙用床上的被子捂着伤口,用枕头垫高。谭勇全身抽搐了几下,几分钟后就没反应了。
她呆坐在旁边的地上,不知道过了多久,她事后回忆说,“整个人都蒙了,大脑一片空白”。
她曾想过报案,又怕报案后对自己不利,就想把尸体弄出埋了。可是,尸体太重了,她弄不动,就想到了分成几部分,再拉出去。她把谭勇的头砍下来,觉得面部表情很吓人,就赶紧把头放进了旁边的高压锅里,随手还合上了盖子。锅里有开水,是她为第二天准备的。天快亮了,才分解完。把东西堆进脚盆里,用纸板盖住,冲洗了厨房,再简单整理了房间。天亮了,有人来买东西,她就把门打开,开始营业。
上午,她把谭勇的衣服和家里的血都洗了,坐在门口绣十字绣。她平时很少有笑容,没什么表情,所以,当天小卖部的客人都看不出她有什么异样。下午,她想着回蚕商局宿舍拿拖鞋,就把谭勇的内脏和生殖器官用一个塑料口袋装着,打了一个三轮车回去。找不到地方扔,就丢到公共厕所里。
她心里非常恐惧,很想想找个人说一说,问问应该怎么办。她想起了老朋友杨,他曾进去过看守所。她认为,可能他会懂。她先去给手机充了值,下午两点多打通了电话,叫他来安岳县。在电话里,她没解释原因,只是叮嘱他,到了以后,用路边公共电话回复给她。晚上9点左右,杨租了一辆面包车来到工地旁边的柠都大道,李彦在路口等他。
上了杨的车,李彦说,“我把谭二娃杀了。”他问原因,李彦只是沉默。
杨说,快去自首。她还是不说话。
杨说,那我去报案。
“你随便嘛”,说完,她下车走了。
等到夜里过了12点,警察还没上门。谭勇被砍下的肢体和肉块已经洗过,放进了三个白色编织袋。李彦一个人呆在屋里,觉得很害怕,决定用竹篼一点点地背出去。
公安系统在不同路段的天网监控视频显示:2010年11月5日凌晨12点多,四周静寂,昏暗的路灯照着砂石道路,旁边是工地的吊机。李彦背着一个竹篼,独自走出安岳县岳阳镇柠都新城二期工地的小卖部。她从柠都新城的工地走到岳阳镇政府,经过南门桥,走到县武装部,财政局后,顺着人民医院,走到城南河边,到达解放堤段。她把竹箩的编织袋拿出,从河边捡了两块石头分别装进编织袋里,把两个编织袋丢进河里,沿路返回。过了一会儿,又背着竹篼,沿着同样的路线,用同样的方法丢进河里,最后返回。
凌晨2时左后,杨带着几个警察开车去了工地,小卖部的门锁了。突然,在前面房子的角落,有一个人影晃了一下,就不见了。警察赶紧跑过去,围着房子,追到后侧,发现有一个人站在墙角,用手电筒一照,是李彦。
警察问,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她什么也没有说,只是重重地叹气。
5
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
电话(Tel):010-84833270/84833276 传真:010-84833270转811
网址:www.woman-legalaid.org.cn 邮箱:ngo@woman-legalaid.org.cn
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108号千鹤家园3号楼1304室邮编:100029

官方微博

微信公众号
©版权所有: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网站建设:中企动力 北京二分 京ICP备11048134号